余南平:新型大国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
来源:文汇报
转载链接:http://wenhui.news365.com.cn/ewenhui/whb/html/2014-04/21/content_56.htm
新型大国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
余南平
今年以来,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系列政策的负面性和曲解性解读明显增加。其中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Graham Allison在1月1号发表在《国家利益》杂志上的“2014大战之年?”最为有代表性,该文不仅提到了让西方政治家无法释怀的“修昔底德陷阱”,同时其还反复描绘1914年大战前的欧洲与今天亚洲的相似之处。在2月结束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连一向乐观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慎重地对亚洲中日对峙的局势表示了忧虑。布热津斯基2009年提出的中美“G-2”概念,哈佛大学佛格森提出的中美“生产-消费”共生关系,这些能够促进中美和谐共处观点的影响力,似乎正在美国弱化。而突破“修昔底德陷阱”,有赖于世界主要大国对时代特征的正确把握与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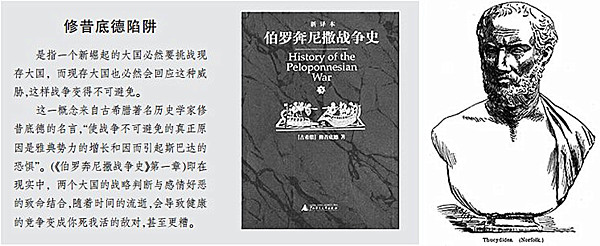
“修昔底德陷阱”的悖论前提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广为西方政治家熟知,要想抹去“修昔底德陷阱”在西方政治人物和学者脑海中的印记,无疑是让他们忘却西方文明开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回顾历史,我们必须看到,在修昔底德的古希腊时代,一是没有今天全球化环境下的国际产业链分工;二是没有国际法约束,武力成为那个时代频繁使用的工具。还有一个不同点是,当年雅典通过“提洛同盟”控制海上航路,并和波斯帝国进行航海争霸战争,表明那个时代,海上航路控制意味着自身贸易的特权和超额的国际贸易收益,而这在今天的全球化自由贸易环境下显然已不存在。虽然今天的海上航路也意味着某些特别收益,但今天埃及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包括巴拿马控制的运河本身,也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超级霸权与经济的持续繁荣与强大,相反美国退出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并没有妨碍美国成为当今的世界强国。
二战后国际发展历史证明,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因为控制了重要的海上航路,而带来特别国际贸易收益权与地区,包括国际霸权。因此,历史进步和经济发展证明的“修昔底德陷阱”悖论是,在今天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依靠相对比较优势整合的环境下,一个新崛起的国家,无需通过领土疆域扩张去证明自己的强大,也无需控制海上航路来维护特别收益权,它仅需要发挥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相对优势的产业分工,而这个分工是二战后全球自由竞争的结果。举例而言,2012年全球占有率第一的产品数量中,中国有1485个、德国703个、美国603个,中国产品主要集中在毛皮、橡胶、旅行用品等全球低端产业。
事实上,我们无需更多指责,当年雅典民主制度下的“提洛同盟”形成的“无疆域帝国”,与今天美国构建的“全球价值共同体”,在政治结构联系上是何其相似。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的古希腊,敌对的斯巴达与雅典之间并没有规模性贸易和体量巨大的相互投资,同时也缺乏两个迥异体制之间的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而今天,全球产业链分工与竞争的形成,已经将大国利益深度捆绑。“修昔底德陷阱”今天的再构造,是冷战思维下的“假想敌”幻觉,不符合大国共同致力于全球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基本时代特征。
今天的亚洲不是1914年的欧洲
与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国际政治格局不同的是,在今天国际格局中,没有当年除英、法、德外的俄国、奥匈帝国、土耳其等势力均等的国家,当年欧洲几乎是多强并列,各自有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民族聚居势力范围,并产生了“联横”的可能。按西方人的历史观念,组成“联盟”,对抗另一个联盟,不仅是古希腊战争史的开端,同时也是西方公国历史习惯的延续。这与中国历史上和今天重视双边外交的“合纵”外交战略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一次大战开始的年代,虽然,凯恩斯不无自豪地认为那是全球化的起始年代,是自由贸易和全球金融自由化的“黄金岁月”。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当年欧洲、或者说当年 “全球化贸易体系”,是以“帝国”势力为纽带和基础的,亚洲、非洲各殖民地为“帝国垂直型”产业链提供了各种可贸易物品,帝国范围越大,帝国收益越大。当时欧洲各权力大国之间,不仅几乎没有规模性的双边贸易,同时更缺乏双向以资本投资和雇佣他国劳动力为纽带的经济联系,国家之间的关系仅仅维系于政治利益和民族同盟,经济关系在跨国关系几乎没有任何重要地位。“帝国势力”延伸意味着强大与霸权。而今天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不仅是全球网格状的产业链,而且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与消费,打破了“帝国垂直”势力体系,同时也在破除民族与文化隔阂之间的极度对抗。
当今世界大国之间,不仅缺乏100年前欧洲有实质意义的,以民族、宗教为核心基础的政治联盟,也缺乏各自附带的保护势力范畴。同时,今天世界主要经济体,不论是以“金砖五国”、“G20”、 “梦幻十一国”命名也好,还是将经济成长迅速的国家统称为“新兴市场国家”也罢,这些经济体自身之间不仅没有稳定的经济联盟框架协议,甚至也没有标准意义上的政治同盟。事实上,在今天的国际关系现实中,政治关系紧密、经济融合水平低下(中俄),政治治理模式差异、经济互融度紧密(中美、中国欧盟),乃至存在领土纷争,但经济交往水平依然很高(中日)的“怪异现象”出现,不仅突破了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战线划分,甚至还突破了历史以“帝国势力版图”为基础的经济联系范式。而这种全球范围内以产业链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以比较优势竞争的新型全球化出现,使得民族、文化、文明、政治的割裂得以有效打破,任何新崛起国家不以地理版图扩张为手段,而是以竞争争夺产业链高端地位和比较优势确立,这一点与欧洲1914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国家认识是完全不同的。
把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
首先,我们认为,要打消中国崛起必然削弱美国影响力这种判断的关键在于,要让美国各界认识到并相信“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提是,过去历史上崛起大国的确是需要以武力开拓疆土,并通过建立各类依附于自身的联盟(政治、经济),来扩大自己势力范围,并提高本国的霸权范围。而今天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已经改变了陈旧的历史发展范式,中国仅仅是依靠自身的经济竞争比较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得了一个恰当的分工位置,中国无需、事实上也不可能通过武力和政治联盟来影响这种分工(如中俄虽有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中俄贸易总额仅为中美贸易额的1/6),全球产业链分工是全球化下国家产业竞争力的自然组合结果,而不是任何国际政治权力安排的结果。中美各自有自身的竞争优势产业,而且中美上下游产业链的组合,不仅有助于全球自由贸易推动,同时还有助于全球福利的共同增加。
其次,在自我战略设计上必须有明确的努力目标。历史经验证明,大国之间贸易联系固然重要,但它是不稳固和不牢靠的,并且是容易被替代的(如目前部分中国制造产品已经被越南、斯里兰卡等低成本国家所取代),而直接投资的关系是最基础和稳固的经济直接联系。目前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FDI)不到70亿美元。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能够达到同等美元规模,直接雇佣几百万美国人并正常纳税,将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何等的正面影响?届时中美各界的直接和间接融合会达到什么程度?所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战略设计之一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尽一切努力扩大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扩大能够带来的深远战略价值,并同时能够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造起到更直接的推动作用。
最后,中美在全球和地区重大事务上均有共同的关切,在某些事务上存在看法分歧非常正常,因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本质不是依附关系,也不是主次关系,更不是对抗关系,而是需要彼此尊重对方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作为基本前提。因此,在中美发生分歧和利益表达不同时,中美双方应该以坦率为基础,主动沟通,包括搁置认识上的分歧,待历史进程解决。而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大的障碍,就是彼此主动设立“对立假想敌”。如美国在亚太推进TPP谈判,这是美国符合自身战略利益的一个新贸易投资框架设计,无论这个贸易投资协定谈判的结果和运营,是否有利于中国,我们绝不能简单假设,这个协定本身就是针对中国的战略设计,是美国精心打造的“围追堵截”中国的工具。应该看到的是,TPP贸易投资协定是21世纪高水平贸易和投资的里程碑,它本身是WTO贸易协定的再推进和提高,中国应该认真研究和学习这个自由贸易投资协定,并以此作为国内扩大开放和各项改革的动力。同样,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坚持维护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坚决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完整,美方完全不应该假设这种符合国际准则的行为是中国实力扩张的举动。维护二战形成的国际秩序,不仅是中国的责任,美国与世界大国均负有历史责任。另外,在涉疆、涉藏,包括台湾等中国内政事务上,美国更不能以“国际裁判”自居,对他国内政任意评价。在国际重大关切上,中美合作空间巨大,而中国的建设性意见表达,绝不应该被美方视为中国在扩展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美国应该看到,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均有平等表达自身意见的权利,哪怕是少数者的权利,这是国际政治民主的基础。大国与小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唯一区别,就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能力的不同,而不是权利的不同。美国不应该误判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和平建设“命运共同体”的设想和努力。
十八大提出“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可以确信的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需要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理论设计,但核心还是马克思早已阐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解决美国一部分人对中国不信任的关键点,必须依靠经济逐步融合手段,而非政治和军事对抗手段。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化的特征已经使得中美产业链高度融合,美国在为全球和区域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的同时,不应该忽视中国作为新兴力量的加入为世界带来的益处,中美更深度的经济融合,符合美国、中国,包括全球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最务实的做法是在已经完成的10轮谈判基础上,尽快完成中美双方投资协议(BIT)谈判。“修昔底德陷阱”的打破,不是依靠假设,而是依靠中美共同的努力行动。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
